「網絡時代,指尖的惡意,是可以殺人的。」
看電影《惡意》時,碰上坊間在熱烈討論張潤衡。事源 TVB 有個重提歷史懸案的節目,透過翻炒歷史片段,加插當年事件相關人士輕描淡寫的訪問,煞有介事的翻叮「舊聞」、口口聲聲尋找「真相」,結果猜與尋也看不到什麼確鑿的新證據與玄機,卻燃起網絡洗版式的怒火,其中網民義憤填膺要揪出 29 年前八仙嶺山火悲劇元兇,矛頭直指張潤衡,他是山火中其中一位生還者。
recommended readings
當輿論成為兇器、鍵盤變成刑具,武斷的正義是否也是一種加害?而我們又是否意識到網絡上的妄言,令我們因此與惡距離有多近?

來牧寬與姚文逸聯合執導的《惡意》,表面上是一部懸疑犯罪片,實則是一場對當代網絡暴力與媒體亂象的當頭棒喝。電影以一宗醫院雙人墜樓案為引,通過資深媒體人葉攀(張小斐飾)的調查,逐步揭露真相如何在輿論下被扭曲,最終演變成一場無差別的「獵巫」行動。電影不僅在敘 事結構上採用了「多視角羅生門」的手法,更在社會議題的探討上直指人心在這個「人人都是判官」的時代,擁有「無形之刃」的我們是否意識到,真正的「惡意」並非來自某個具體的兇手,而是整個社會的集體狂暴?
電影引述了經典著作《現代性與大屠殺》(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)中,英國社會學家 ZYGMUNT BAUMAN(其為有猶 太血統學者)的分析:發生於納粹集中營的悲劇,是因為每個士兵都只是機器中的一個齒輪,機械地完成自己的環節,而不用對最終結果負責,道德的消失點就誕生了。
引用於網絡欺凌事件上,對他人的造謠、污衊、指尖的惡意也是如此,虛擬上帝們以為無關痛癢的揶揄、人云亦云的羊群式指責,累積起來對當事人都是凌遲的一刀。電影有意思是它並未停留在「誰是兇手」的傳統懸疑框架內,而是將焦點轉向「輿論如何殺人」。當葉攀在直播中煽動網友對疑兇的仇恨時,鏡頭切換至無數手機屏幕上的惡毒留言,形成一種「數據洪流」的視覺衝擊,讓觀眾感受到網絡暴力的恐怖不需要刀槍,只需幾句未經證實的妄語與指控,就能讓某君人格死亡。
《惡意》採用了大量新媒體元素:直播畫面、社交媒體彈幕、短視頻剪輯等,讓觀眾彷彿置身於一場現實的輿論風暴。值得肯定是,電影並未給出簡單的道德答案,也沒有站在上帝視角教訓觀眾,而是把每個人都拉進這個信息洪流裡,讓每個人都成為惡意鏈上的一環。「雪崩的時候,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。」恰恰反映了現實中網絡暴力的複雜性:我們往往在無意識中成為加害者。
印象深刻的是,電影中段通過「監控錄像」的視角呈現真相,但不同角色的解讀卻截然不同 —— 這正是「後真相時代」的寫照:所謂「真相」,早已被算法和偏見過濾。
《惡意》最令人不寒而慄的,是它與現實的高度重合。從阮玲玉的「人言可畏」到「張潤衡事件」,無數悲劇證明,輿論暴力早已成為一種社會性兇器。
電影中不少精警台詞:「現在誰還在乎真相?他們只要爽!」恰恰戳中了當代輿論場的現象 —— 我們追求的或許並非正義,而是一場矯情的情緒宣洩。
《惡意》英文片名《MALICE》或許比中文更貼切 —— 因為惡意並非某個具體的兇手,而是潛伏在每個人心中的陰暗面。在流量推波助瀾下,真相被情緒湮滅,惡意被包裝成正義。它正好提醒我們:參與「道德審判」時,是否該警惕自己可能正在成為劊子手?
戲裡一句提醒,當頭棒喝:「發聲之前多想想,再多想一想。」這是《惡意》背後的善念。
recommended readings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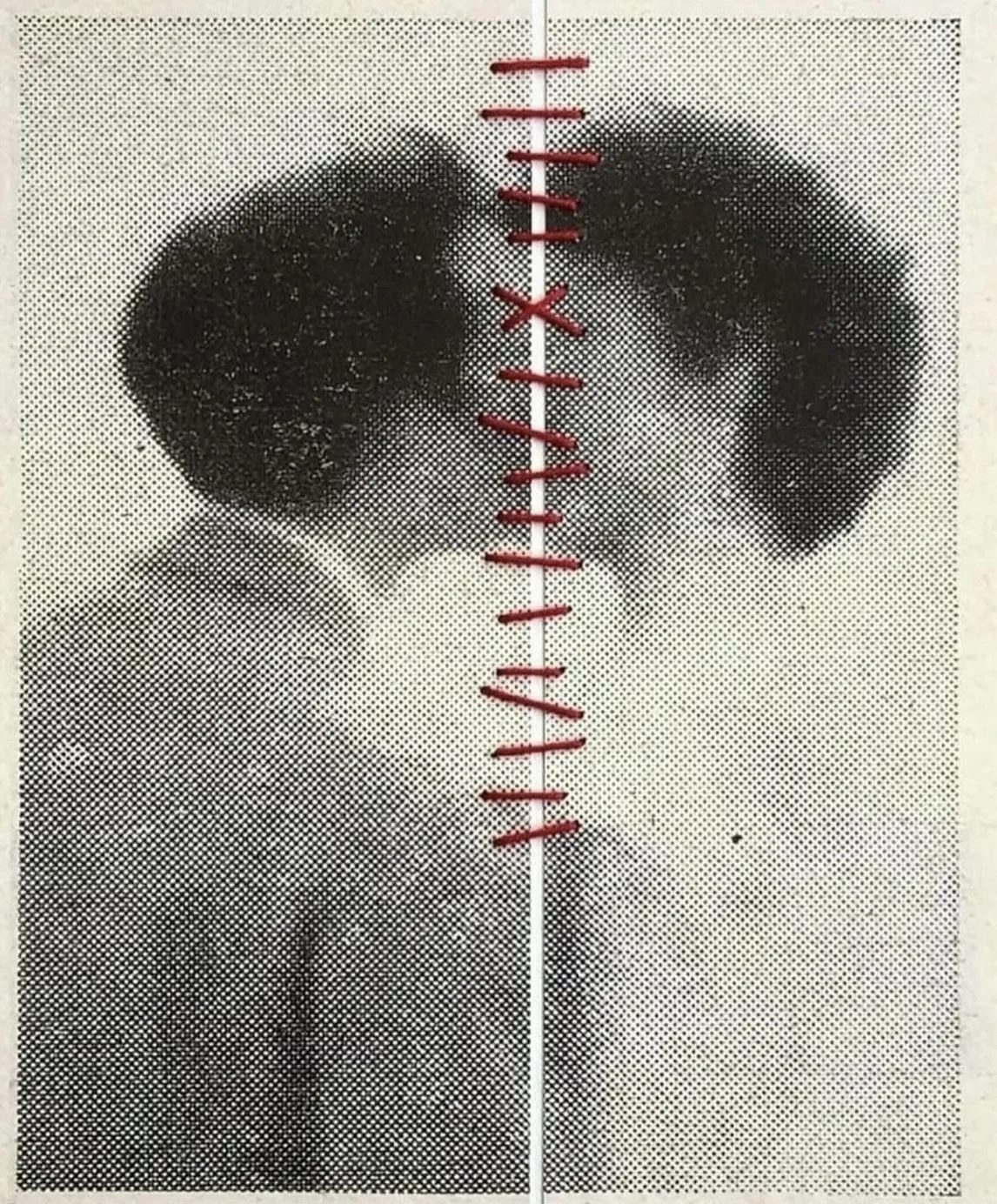








Commen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