專訪多年無見的導演陳可辛,傾開他的新戲《醬園弄·懸案》與電影寒冬,問一向憧憬串流的陳導網絡平台是否出路?聽到的是他對大數據與 AI 等科技洪流衝擊下的自省,甚有警惕性。
「大數據是很恐怖的一件事,如果我們永遠跟著觀眾喜歡看什麼去拍戲,就是在逢迎觀眾昨天的喜好,這就像開車時只看倒後鏡,不看前方。」陳可辛的當頭棒喝,值得引以為戒。
recommended readings
明明成語是「推陳出新」,偏偏大數據像逆水行舟,按你喜好不斷餵食,「推新出陳」。到最後,麻木的我們已不追求新舊,盲目的接收所有的麻木,炒冷飯當九大簋。
在電影產業中,NETFLIX早已憑藉演算法推薦顛覆傳統敘事邏輯,而荷里活片商更習慣透過大數據預測票房。陳導提出的「倒後鏡思維」的危險在於:它將創作簡化為對既有偏好的歸納,而非對可能性的探索。陳可辛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,2007 年他的作品《投名狀》上映時票房未如理想,卻在十年後被重評為「被低估的史詩」。若當年依賴大數據決策,這部挑戰觀眾戰爭片預期的作品或許根本不會誕生。
更深層的問題在於,AI 的數據驅動本質上是一種「路徑依賴」。當 CHATGPT 根據既有文本生成故事,或 MIDJOURNEY 拼貼過往畫風時,它們實質是在重組人類的「文化 DNA」,而非創造新的「基因突變」。陳可辛的電影生涯恰恰證明,經典往往誕生於與時代審美的錯位 —— 從《甜蜜蜜》的移民敘事到《中國合夥人》對中國企業家的解構,他的作品總在挑戰當下的「正確答案」。這種「不看倒後鏡」的勇氣,正是 AI 迄今無法複製的創作者直覺。

最近在香港認識英格蘭藝術家 DARREN ALMOND,他的作品向來對時間、記憶與場所的不穩定性之深刻探索。見他完全沒有社交媒體,好奇問他對 AI 創作的意見,他搖搖頭,平靜地拋出一句曾被康城引用的對話:「媒介從未超越藝術家,是藝術家超越了媒介。」(THE MEDIUM NEVER TRANSCENDS THE ARTIST. IT’S THE ARTIST THAT TRANSCENDS THE MEDIUM.) 這句話一石激起千呎浪。
陳可辛與 ALMOND 創作於不同維度,卻在 AI 狂潮中互相呼應:真正的創作,永遠是一場面向未知的冒險,而非對過往自己的馴服。
ALMOND 之言我認為是對 AI 工具的優雅反擊。以他的代表作《FULLMOON》系列為例,那些通過長時間曝光捕捉的月光風景,本質上是對「時間」這一媒介的重新詮釋。這種創作需要藝術家對自然、機械與哲學的獨特理解,絕非簡單的技術疊加。他認為藝術家的職責就是超越(TRANSCEND),無副業。
ALMOND 的「超越論」揭示了一個悖論:當 AI 越來越擅長模仿既有風格,藝術家的價值反而更體現在「破壞模仿」的能力上。譬如畢卡索摧毀透視法則,都是對傳統的主動背叛。陳可辛與 ALMOND 提醒我們:當技術讓表達變得太容易,真正的挑戰反而是如何不被表達所奴役。
這方面,日本動畫導演押井守的實踐頗具啟發性。他在《攻殼機動隊》中大量使用數位技術,卻堅持手繪分鏡,因為「科技應擴張想像力,而非替代思考」。同樣地,TRANSCEND AI 這家致力於用 AI 化解國際衝突的組織,其創始人OLA MOHAJER 強調:技術必須服務於「人類的決策主導權」,而非反客為主。這種「科技人文主義」的立場,或許是創作者面對 AI 時的最佳態既不大驚小怪地排斥,也不盲目樂觀地擁抱。當演算法能完美計算觀眾的淚點與笑點時,藝術最珍貴 的恰恰是那些「不完美」的設置。
ALMOND 的「超越論」與陳可辛的「倒車鏡警告」,最終指向同一 種創作倫理:真正的創新永遠需要直視前方的黑暗,而非倒後鏡中的光明。就像梵谷生前只賣出一幅畫,卻為百年後的我們點亮星空。 這或許正是 AI 永遠無法「超越」的奧秘:人類的偉大,在於敢於為尚未存在的觀眾創作。
recommended readings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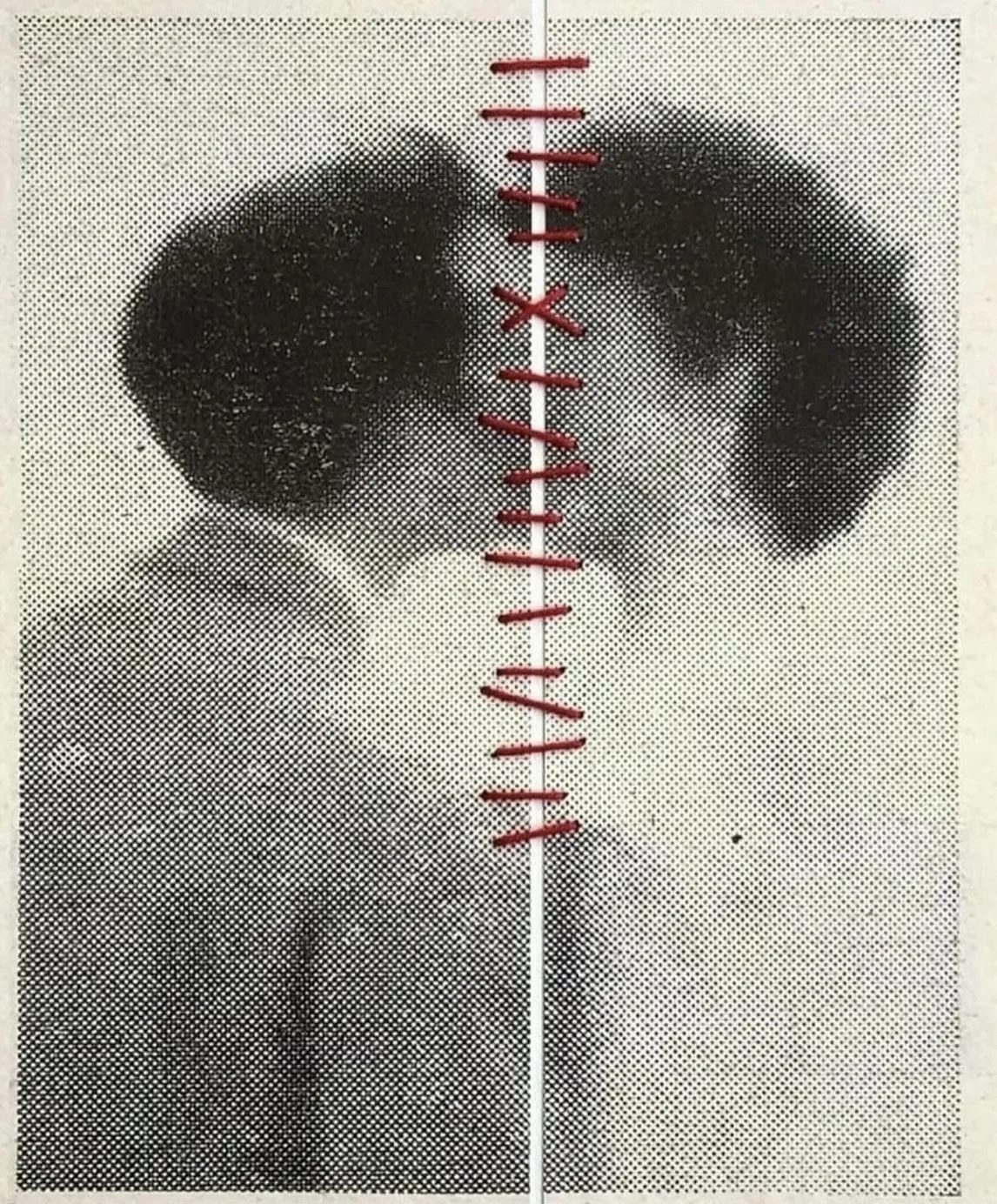








Commen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