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事說收工去廟街睇相。對於她去睇相,我自然沒資格說三道四,問題是她去看的那個文師傅偏偏是個「作家」;對於這個文師傅將睇相當創作,我當然也沒資格說三道四,問題是他索我同事 8,888 元,而這數字相等於她半個月糧;但對於她心甘命抵將半個月的血與汗雙手奉送給一個創作人,我也是沒資格說三道四的,就算她要拿金牛餵大笨象,我也沒有。
但我可能有道德責任勸她回頭是岸。
這一刻,她就站在我面前,歪起頭,掛著好奇的微笑,等待我發表意見。我可以這樣說﹕「嘢可以亂食,錢唔可以亂使。」或者說﹕「有沒有考慮過助養兒童?⋯⋯不,不是宣明會也可以。」然而為甚麼我仍然甚麼都沒說?

因為那個文師傅是我堂哥。
他有一個古雅的名字,文曲。
「文曲,別喝了。」
「文曲,喝醉了伯母又要來怪我。」
「文曲,酒量淺還要飲酒是犯罪,你知道嗎?」
「我不是很清楚。」某夜他打了一個很長的嗝,然後說。「相士!」
「好,好,相士……甚麼相士?」
「問得好!甚麼是相士?」
「??睇相的士?」
文曲舉手一揮。「相士的口頭禪是甚麼?」
「施主,贈你兩句。」
他用力點頭。「正確!何以相士總愛贈人兩句?」並不等我回答便繼續道﹕「LET’S SPEAK ENGLISH.『贈你兩句』。 “I GIVE YOU TWO SENTENCES.” 洋人聞言想必誤會 I AM A 作家、詩人,NOT 相士,對吧?」
「嗯⋯⋯」
「故相士者,詩人也,作家。」
「可是,睇相不是創作吧?」
文曲擺出一副「兄台你有所不知」的樣子,長嘆。
對於相學和文學我確實一無所知,除了知道算命師傅王貽興以前也搞創作。王師傅二十出頭便拿文學獎,而文曲出道比他更早。小時候的他已是才氣橫溢,十四歲便在文學雜誌寫詩,中學未畢業便出書,一本詩集,叫《綣紗纏》。大學在中大念中文。我也念中大,不過念的是電腦,但即使了不相干,我也曾經好多次在走廊與飯堂耳聞他的傳說,比如他如何在迎新營的才藝晚會表演七步成詩;傾慕他的女孩是如何多,好比大海裡的魚;而他又是如何秒速換畫(到現在仍是)。畢業後他一度在文學界打滾,寫專欄,後來有人找他進軍娛樂圈,主持清談節目,被他拒絕(這點與王貽興不同)。我曾經問過文曲為甚麼,他說﹕「我是作家,又不是戲子。荒天下之大絕謬!」
至於為甚麼作家上電視荒謬,睇相就不荒謬,他有他的解釋,雖然我不是很有自信搞懂。據他說,作家的要務就是寫出打動人心的作品,讓讀者深感那些精雕細琢的言辭講中他們心坎裡頭最真摯的慾念、悲傷、渴求、憤慨,讓他們懷疑作者是不是偷窺過他們的人生。而相士相同。每個客人睇相,帶來的都不只有問題,還有這些問題的答案,只是問題由他們自己開口說,而答案則埋藏在內心,等候相士替他們講出來。
「睇相其實是照鏡,讓人直面他們內心那真實的模樣。」文曲說。
我對他的怪論一直不置可否,本來也是不必置可否的,畢竟這事跟我無關,就算他去給拜登睇相收他8,888鎂也跟我無關。沒想到今天卻因為有同事成為他的客,令我不得不有個論斷﹕到底文曲是強詞奪理還是強詞有理?站在同事面前我苦苦思索,可惜苦苦苦苦時,同事已經走了。
「哈哈哈你怎麼沒反應。」她揮手。「明天見﹗」
我唯有想像她把 80 張 100 元、8 張 10 元和 8 個 1 元,拿去海洋公園餵大笨象⋯⋯直至翌日。
翌日上班我發現兩件事。第一,海洋公園沒有大笨象。第二,同事在辦公桌的水松板正中央,用四口大頭針釘起一張宣紙,紙上是兩行詩。
舟火幽幽夤夜行 長路綿綿尋不停
近水樓台縱無聲 遠航渡頭人自明
「這是甚麼意思?」我問同事。
她悄皮地舉起一隻手指,朝天花板指兩下。「天機不可洩露。」
我皺眉。「是妳不告訴我,還是文曲沒有告訴妳?」
「嘿。」她對我做個鬼臉,然後擺出一副 I KNOW THAT FEEL BRO 的表情。「你古惑了。」
「甚麼古惑。」
「我不記得自己講過他叫文曲,只說他叫『文師傅』。」
「呃⋯⋯」
「你偷偷搜過他的資料,對吧?怎樣?要不要傳你這個。」她高興地拿出手機給我看螢幕上一張八折優惠券。隨即又撥到一張照片。照片上有兩個人,一個是頭髮梳得整整齊齊、鬍子刮得乾乾淨淨、穿著富有時尚感的漢服的文曲,另一個則是眼睛裡頭有一百萬個心心的她。
「我宣布要跟 ANSON LO 離婚!」她說。
我聳肩。
回到自己坐位後,我給文曲發訊﹕
狂賀閣下又成功騙得一枚狂蜂浪蝶
09:59
昨晚那女生?
10:02
我同事
她要跟 ANSON LO 離婚
求大師放過無知少女
10:05
呵呵
10:06
笑甚麼笑⋯⋯
10:06
墨點飛揚作屏風 一人稱山另稱雪
玉蝶縱戀畫中花 何必苦撈水中月
10:07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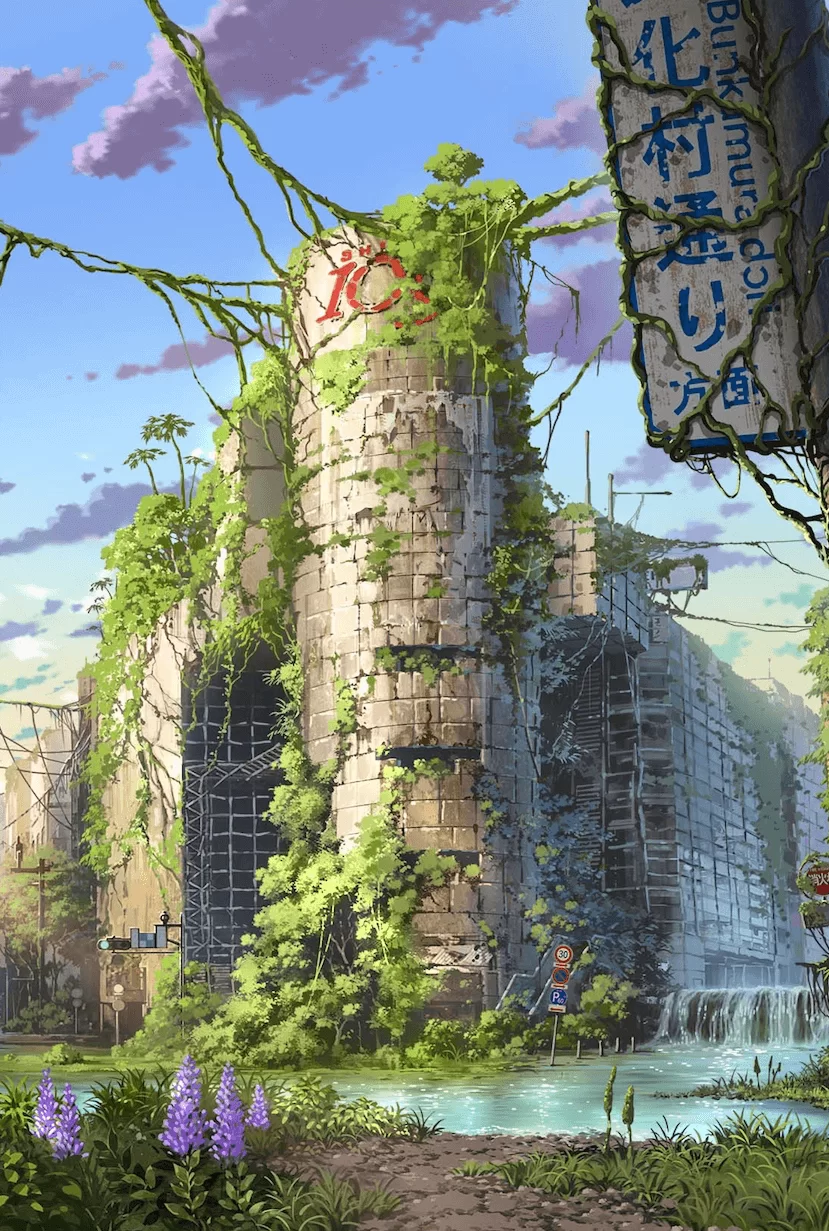




Comments